在空隙中: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智能广告生产——关于苏特·杰哈利《广告符码》的讨论
刘施阳
2025-09-02 17:57
![]()
本文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通过对苏特·杰哈利《广告符码》理论的批判性回顾,重返20世纪广告发展史,在历史语境中还原“广告收看劳动”与“观看广告时间”两个核心概念,并在智能广告实践中重新打开。借此在商品与广告、我们与广告的“空隙中”探讨智能广告生产的本质。

摘要
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元技术变革下智能广告蓬勃发展。从“技术伺服系统”的追问,到“弗氏人偶”的寓言与想象,这背后活跃的人与智能广告的关系值得反思。要把握今天智能广告丰富而复杂的实践,需要回到广告技术发展的历史脉络中解释自身。本文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通过对苏特·杰哈利《广告符码》理论的批判性回顾,重返20世纪广告发展史,在历史语境中还原“广告收看劳动”与“观看广告时间”两个核心概念,并在智能广告实践中重新打开。借此在商品与广告、我们与广告的“空隙中”探讨智能广告生产的本质。
关键词
智能广告 程序化创意 广告发展史 劳动价值论 广告批判
Abstract
Under the meta technological changes such as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lligent advertisement is booming. From the questioning of “technical servo system” to the allegory and imagination of “the Freudian robo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intelligent advertisement is worth reflecting on. To grasp the complex practice of intelligent advertising, we need to go back to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of advertising technology to explain itself.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economy, through a critical review of Sut Jhally’s theory of The Codes of Advertising , this paper returns to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advertising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restores the two core concepts of advertising “watching labor” and “watching time”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re-opens them in the practice of intelligent advertising. In this way, we can “in the space” to discuss the essence of intelligent advertising production between commodities and advertising, between us and advertising.
Keywords
intelligent advertisement programmatic creative history of advertising labor theory of value critique of advertising
1.智能广告的秘密:从技术伺服、弗氏人偶到广告符码
智能广告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元技术变革广告业态的核心表现之一是创造并高度智能化发展了程序化创意[1]。在2023中国国际广告节上,阿里妈妈旗下电商AI创意生产工具“万相实验室”借助这轮变革,实现电商直播广告的全天、全流程的程序化创意生产,自动抓取、决策、生产、投放、传播。广告生产者通过程序化流程,在平台完成广告内容与形式的模块化组建,在供需双方互动与反馈中调适、凸显产品特色,进入市场,吸引用户,最终达成消费。在既有智能广告研究中,程序化创意在技术层面上被广泛谈及,但尚未形成较为统一的定义。段淳林、任静将其视为智能算法基础上广告生产与用户需求的自动化、个性化精准匹配的创意生产机制[2]。张景宇则强调它是一种投放与优化同步的创意推演机制[3]。丁晨洋、冯广圣指出其系统整合与动态重组的特征,划分为深度与浅度的程序化,深度程序化则具有基于大数据产生的系统性联动[4]。如秦雪冰指出,以程序化创意为技术表征的智能广告生产,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技术嵌入与价值取向构成其演进的原动力[5],如工具化、数据化、人性化等。综上,以程序化创意为表征,学界普遍认为智能技术变革使广告生产呈现出一种新的范式。但正如陈刚所说,当既有作业模式被改变,必须追问的是技术的价值与将来的方向[6]。程序化创意中的“创意”来自哪里,又去向哪里?自动化、个性化、精准化等技术范式的革新意味着什么?两者之间又有何关联?
经上述阐释,程序化创意(programmatic creative)是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多样化、自动化组合、调配广告内容与形式,精准用户匹配的智能广告生产方法。因此,它表现为更彻底、更个性、更精准、更自动的创意模组与广告生产,这背后是智能广告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革新。回到程序化创意的技术原点,程序化创意的所有技术设置都精准锚定用户需求,通过将需求点碎片化、标签化形成模组和数据,从而更全面、精准、强力地吸引用户,达成消费。因此,程序化创意中“创意”的提取和生成过程,可以理解为将人(用户)对象化、客体化的过程。人的需要与欲求被数字化为广告生产的模组和数据,被“抽离”并命名为“创意”工具。这个过程,与其被表述为“以人为中心”的生产过程,毋宁表述为“以吸引用户为中心”,通过人的客体化,完成广告生产的过程。这才是程序化创意中“创意”的来源和去向,而技术机制的自动化、精准化与同步化也相应代表着人及其需要的客体化、对象化,从模糊到精准,从手动到自动,从滞后到同步的过程。但部分学者将程序化创意的上述过程,表述为智能广告生产的“人本主义”倾向,如“利用用户触点交互”的“用户本位”思维[7]等。有学者也关注到智能广告生产中“颗粒化掌握用户需求,基于用户时空感知”获得“深度沟通能力”的过程,本质上是“去主体化的高度自动化状态”[8]。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揭示技术“自动化必然以伺服为前提”,即人整体反映世界的知觉和信息被客体化储存。这个过程就是“技术的伺服系统”,“由于持续不断拥抱技术,我们成了技术的自动伺服系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只要使用技术,就不能不为技术服务,人的延伸物会被当作神祇或小型的宗教偶像来崇拜”[9]。在“自动化”的过程中,商品(广告)既具有了可感觉又超感觉的“拜物”的性质[10],但同时又是虚幻与异化的。在这样的“数字系统”(或称“符号表意系统”)中,刘禾的《弗氏人偶》寓言般指出“凡不能脱离人机拟像无限循环,继而不能摆脱控制论的无意识的网络化的存在”就会沦为“弗氏人偶”,即弗洛伊德机器人(Freudian robot),一种习得于人的特性,但最终又在技术的强迫性重复下沦为无意识的“非人”存在。无论是麦克卢汉对人与技术主导既热衷又批判的摇摆,还是刘禾看似“极端”却充满想象的批评,都在昭示今天的智能广告生产并不只是技术变革广告生产效率这么简单的技术事实,这背后活跃的人与智能广告技术的关系值得反思。
既有智能广告研究,停留在技术变革与广告生产现象的表层,较少关注到智能广告生产逻辑,智能广告与人的关系,缺乏跨越智能广告技术、广告批判研究、商品与符号的政治经济学等单一范畴的理论工具。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脉络中,苏特·杰哈利在《广告符码》中对20世纪广告生产的本质、生产逻辑及其与人的关系,以及新广告技术产生的拜物教现象已有较为充分的讨论。但如何在智能广告时代重新清理杰哈利的理论遗产,借此重新反思智能广告生产的本质、生产逻辑,以及智能广告与人的关系,是本文尝试完成的任务,也是目前广告研究学界共同面临的挑战。
2.杰哈利的遗产:保卫马克思与挑战马克思
苏特·杰哈利的《广告符码》基于20世纪西方消费社会的拜物现象,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广告生产及运作实质进行分析。他像马克思理解资本主义先理解商品一样,通过广告,这一劳动与商品的中介,去理解19—20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提出收看电视就是雇佣劳动,以此破除以信息为焦点的讨论方式,将20世纪美国电视广告纳入交换价值系统中考察。提出以受众观看广告时间作为受众劳动时间,广告商(广告生产者)通过延长绝对广告时间提高绝对剩余时间,通过分割广告、使广告更密集、依据时间段匹配等手段提高相对剩余时间,以此提升广告对此商品的剩余价值。从物神、马克思拜物到弗洛伊德拜物,将广告放置于人与物的关系当中去讨论,审视广告符码,即商品作为物的本身意义被资本主义抽空,广告就成了中介,填充了“空隙”。
广告的批判研究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术脉络的关键,在加纳姆看来,广告是商品生产和交换创造剩余价值的媒介,斯迈斯则指出受众观看广告就是为商品劳动的过程,受众注意力被打包售卖给广告商,而杰哈利是将交换价值聚焦于受众时间来考察,他认为斯迈斯的“受众商品论”最终沦为受众个体的主观结果,这与唯物论者注重客观的物质性相抵触。因此他在对斯迈斯理论的扬弃中锚定了自己的理论位置——将广告放置于交换价值体系中考察受众的观看时间,来理解西方消费社会的资本主义体系。斯迈斯认为受众以购买力做了工被售卖给广告商成为了雇佣劳动。但杰哈利意识到广告商花钱购买与受众购买力之间没有直接关联,无法保证受众看后就会产生购买力。因此杰哈利发展出“收看时间”的概念,受众向商业媒介出售的商品形式是他们的时间,更准确地说是“传播所界定的时间”。他认为广告商能够售卖是以传播资料为表征的生产资料,这也是他们唯一能够控制的。杰哈利通过当时的经验研究验证了这一理论的有效性,并将受众时间理论嫁接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时间之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是人的劳动是社会生产力的基础。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只与劳动相关而同生产资料无关,因此杰哈利将广告放置于交换价值系统中考察,而非使用价值系统。此外,杰哈利从广告生产角度,指出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本质就是物的异化,意义被抽空,广告得以进入填充空隙,也成为了空隙。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既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延续和保卫,也是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正面挑战。
也正因如此,广告符码理论在当时便引起了较大的质疑和批评,其中最大的反对声是,收看电视节目不同于工作劳动,不能与工作劳动等同。在经济生活中,工作劳动属于被迫劳动。彼时学者指出受众观看电视节目“完全可以自由停止收看,这样也就停止了为媒介生产剩余价值”[11]。杰哈利也曾对其将收看活动类比工业劳动的不准确进行自我批评,指出这一理论易于引发歧义之处在于他将工业劳动作为模式,或称形式,事实上工业劳动生产的是物质体,但收看活动中的生产与交换往往是无形的[12]。迄今,学界有关该理论的批判主要集中于两点,第一,观众观看劳动不是强制性的,不能与马克思的劳动等同看待。第二,马克思讨论的是工业劳动形式,虽然马克思也说“文化工业”但性质仍然不同。但斯迈斯与杰哈利的劳动价值论始终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今天的文化是工业,是工业时代的工业劳动。杰哈利以观众的上瘾、时间的殖民化等观众行为和心理上无法摆脱的例证来支撑其观看劳动强制性的观点。刘小新认为这无法从学理上给予周密的诠释,所以他只能退守到经验例证中[13]。国内学界对于广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经典文本外的发展并不多,且部分研究缺乏历史维度的考量,批判也因此落入窠臼。无论是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视角,抑或从智能广告的时代视角,都能对该理论提出各种各样的批评。但批评本身并不是目的,关键在于借助不同视角得以更逼近今天中国正在发生且势不可当的智能广告生产。
在智能广告时代值得追问的是,受众能“完全自由地停止观看”吗?受众时间由“媒体与受众共同生产”?受众时间理论是否依然能全面反映用户、广告与剩余价值的关系?如何看待用户对广告所做的功?在今天智能广告时代,是否观看、什么时候看、看多少、看什么,在很大程度上都不是用户可以决定的。在智能广告算法中,虽能点击关闭、不感兴趣、与我无关等反馈,但其本质是强迫对广告及产品产生互动和反馈,目的是推荐更多、更能构建你需要的广告和商品。杰哈利以观看时间作为度量剩余价值的尺度,但今天智能广告的观看时间呈两极趋势——极长和极短的观看,极长的观看,就是被吸引、喜欢那符合观看时间的尺度,但极短的,转瞬即逝的广告,或者点击关闭反而记住了它,其产生的相对剩余价值可能和极长的观看是一样的。在这个层面上,观看时间无法完全解释今天广告所产生的剩余价值。基于智能广告超越时空、无所不在、无法不响应的特点,该理论在今天的效度需要重新讨论。唯有重返历史语境,理论才能解释自身。因此,重返20世纪,重新理解广告的生产与发展,媒体如何参与受众时间生产,是理解今天智能广告生产逻辑的必由之路。
3.时代后视镜:重访20世纪广告发展史
今天以程序化创意技术为代表的智能广告以产品为中心的生产趋势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西方广播电视广告时代。重访20世纪广告发展史,将“受众商品论”与“收看时间”等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还原到历史语境,作为今天智能广告时代反思的基点。
当时遥控器、“杂志形态”广告等技术和技艺的变革,使得快节奏的广告成为可能。广播与窄播(有线电视以特定观众为对象,其中部分按片付费)则再次推动广告变革,其根本动因是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版图在媒介领域没有得到充分满足,主要媒介溢出的剩余价值无法与资本主义日益膨胀的欲求相匹配。如何通过广告的变革带动攫取更大剩余价值,如何满足资本主义膨胀的欲求,更直接的问题是20世纪广告技术变革的本质是什么?
在这个层面上,马克思关于“纯粹流通”的讨论,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广告的诞生及技术变革的本质。由于卖者在市场上奔走达成交易的时间,是经营时间中所必须的“买卖时间”“能量消耗”和“劳动时间的扣除”,因此当卖家“具有规模”后便可以不再亲自从事“燃烧劳动”,“而把它变为由他们付酬的第三者专业”[14]。第三者专业本身是非生产的,却是再生产的必要因素”,出卖自己的劳动,但又不创造价值,执行并服务于纯粹流通职能[15]。因此广告自诞生之初其目的便是帮助商品达成交易,实现商品到货币、货币到商品的转换,与其说广告服务于消费并以其为动力源,不如说广告真正服务于异化了的社会消费、异化了的人的需要,这部分才是广告在高度市场化环境中得以存在和生产的真正动力源。这点是20世纪广告繁荣发展,今天智能广告生产与技术变革所共通的底层逻辑。
回归广告本身,广告作为商品与市场(用户)的中介,同时接收两端的规制,广告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映照或先导。为了在高度市场化环境中达成商品的流通、交易,20世纪广告发展史产生了两个重要结果:一在广告生产诉求上,从价值的直接陈述,转向对隐喻价值与生活形态的塑造;二在广告生产形式上,视觉影像取代文字说明成为现代广告传播的主宰元素[16]。两者的叠加使用户对广告背后产品的关注度提升,构建起关于产品强大的联想链(strong associational link),同时保持着相当程度的暧昧(ambiguity)。但广告所产生的暧昧,一方面使得用户不仅产生满足的感觉,还会在满足与不满足的欲求中陷落;另一方面用户对产品会发散出广告生产者无法完全掌握的想象,联想的边界往往模糊,甚至无边界,这使得很难与直接、必须的市场(用户)需要联系。因此,莱斯提出“需要与商品的双重暧昧”[17],指出了广告生产要针对和解决的痛点,这也是20世纪广告生存与发展的根基。广告作为连接需要与商品的中介,其价值取向、类型与场景、市场与营销策略等多面变动,都服务于二者。恰恰因为多重暧昧的模糊与规制,今天智能广告生产的程序化、模块化直指人的碎片化需要与商品特色(非质性)[18]相贴合,构建起可看性、趣味性,用户(买者)在观看广告中收获的体验感、满足感、获得感。这个过程中的广告生产逻辑与20世纪电视节目以自身作为与受众收看能力的等价交换是同构的,即“传播产业的可变资本”[19]与作为受众商品的时间与行为交换。
无独有偶,利万特也曾对广告发展进行历史性追踪,指出“广告讯息历史性地从强调物质功能为中心……转移到强调人的欲望为中心……又转移到强调个人与小群体的生活方式……最后转移到强调在整个社会形态中,物我一体的感觉。”[20]当广告发展的转变,置于历史语境中人与物的关系上,不难发现,每次转变实非巧合,更不是“历史重复的兴起”,而是有意雕琢。如杰哈利批判工业文明所暗示的,是新旧时代、新旧文化两者间的互相琢磨,而琢磨会导致很多地方出现空白。此时,广告作为中介与填充物,便会迅速地进入、填充、抹平,像如从未发生过一般,成为新的“真实的陈旧的”印记。相较于传统广告所建构的时空,智能广告趋近于时空无限的延伸和拓展[21]。同时,它也更迅速、更不易察觉,甚至还没发现、还没感知到就已然在空白处凭空构造出了一个包裹了概念、产品的广告。
4.忘掉杰哈利:智能广告时代的收看劳动与观看时间
通过对苏特·杰哈利《广告符码》理论的还原与回顾,可以看出,该理论在破解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在技术变革中新的广告范式,大众与媒介丰富而复杂的广告实践,具有重要的建构意义。杰哈利的广告理论,既以此为历史前提,也是西方这一时代的见证和表征。但在智能广告的今天,不得不面向元技术带来接踵而至的“奇点时刻”,杰哈利有关理论是否成立?中国的智能广告生产如何能够获得新的理解?这是迄今为止并未取得足够新进展的重要话题。今天苏特·杰哈利与其理论在广告研究中的消逝,恍如彼时,鲍德里亚在“大众冷漠”中高喊“忘掉福柯”,这是当面说出“理论的过时”,试以新的方式重新唤醒。让·布希亚呼喊“忘掉福柯”,是直言新语境下理论形式与内容的不一致,呼吁破除理论表层的幻觉,重回核心关切。如鲍德里亚所说,忘掉他,“一切与压抑无关,一切与生产有关,一切与压制无关,一切与解放有关。”所以,本文在回顾苏特·杰哈利理论脉络后,试在智能广告生产中,重新打开其理论的核心概念——收看劳动与观看广告时间。由此,也许才能走向真正“忘掉”的反面——坦白与去蔽。
在智能广告的生产语境上,与广播电视广告的诞生不同,智能广告是数字时代碎片化的产物——高度市场化环境导致个体与外部环境分离,个体内部人格破碎,甚至碎片到难以拼接“维持在一个完整的层面”。这是20世纪广告发展的困境和机遇。但这是今天智能广告生长无法回避的普遍现实。如上述阐释中广告的暧昧性本质,模糊与碎片对应着勾连起更广大群体,而具体与完整则对标的是清晰的个体。此外,受众“在消费上花的时间越多,对各个欲求就越不在意”[22]。如若广告只抓住个体,就难以在整体上清晰分配、描述欲求,抓住人格碎片化带来的瞬时欲求才是达成消费的关键。因此,广告强调人们能够被商品在一瞬间“固定”住,然后购买解决现代生活问题[23]。智能广告高自动化、高精准化的程序化创意就是以抓住瞬间效果构成其生产与传播的原动力。此外,日益加剧的市场竞争,使商品的物质关系与符号关系变动不定,这就要求商品的符号形象也要保持变动,不断弥合商品两重属性变动导致的消费与需求渐次分隔的距离,以满足不同场景和用户的“瞬时需要”。
在智能广告的生产方式上,要在碎片语境中,生产符合瞬时需要的商品,使商品符号化是广告生产的重要步骤。商品的符号化,不单是关于商品的消费方式,也涉及商品与广告的生产方式。正如杰哈利风趣地揭示“如果商品能说话,它们会说,我们只不过是物体,我们的使用价值也许会吸引人们,让人们对我们感兴趣,但它并不属于我们。”[24]因此,“是人与物的关系界定了使用价值,产品对我们有用,并不在于产品本身,或产品的属性”[25],是广告为物的有用性赋予了符号意义。简言之,广告使商品符号化所产生的符码,本质上是作用于人与物的关系上,而非物本身及其属性上。“生产已被架空,广告重新填充”[26],人在与商品的互动过程中,需要有关商品的意义。而广告为商品赋予意义的幻觉,其真实与虚假并非最根本的问题,更本质的是,广告赋予的符号意义是在商品生产意义被掏空的空地上成为了统治者。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商品的交换价值支配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这个过程中,广告生产的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有两次“纳入”(subsumption)[27]。“subsumption”在中译本被翻译为包容,包容一次在中文中较为含混,两者的关系因为“包容”这一语词而变得暧昧不清。事实上,杰哈利使用的“subsumption”在英文原义中是后者被前者包含或纳入其中,从而成为前者的一个次级前提(小前提),这个语词中内在了两者间的逻辑与关系。这点有助于厘清杰哈利理论中广告生产中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因此,本文选择选用“纳入”这一翻译,强调后者被前者在商品符号化与生产过程中,被重新整合作为次级前提包含其中。具体来说,两者第一次纳入发生在生产领域,广告中商品的各种社会关系掩藏了其生产关系中,也因此掩藏了商品真正的、完整的社会意义。即今天无论是在商品还是广告上,我们都无法真正且完整地看到除了特色、质性外的有关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信息,如谁在什么地方,如何生产等。第二次纳入发生在传播领域,广告信息的形式与内容受到用户劳动的交换价值制约。基于以上两点,杰哈利选择将广告生产置于交换价值体系中考察。马克思指出“每个商品的价值是由物化在该商品使用价值中劳动的量决定的,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28],而使用价值是商品“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29]。这是为什么杰哈利要用收看劳动与观看广告时间两个概念来破解交换价值体系中的广告生产。因此,要在杰哈利的理论框架中,将智能广告置于交换价值体系中,就必须考察它的劳动与劳动时间。
在智能广告的用户收看劳动上,有学者指出广告的“收看劳动”不是强制劳动,也不属于工业劳动。马克思曾较为模糊地论述过“文化工业”的概念,还原历史语境,收看劳动的确不属于工业劳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收看劳动本身理论价值的全盘否定,需要思考的是在今天收看劳动是否具有新的阐释可能。收看行为本身,意味着对不同媒介中数字广告内容的接收与互动,在这个意义上,是否也可以被视作一种服务于广告生产的劳动。此外,智能广告的生产方式,可视作资本不触动其他生产关系,只是把旧有的生产关系纳进自身的运作中来,接管较为陈旧的广告生产模式的工具或称手段。换言之,生产工具的革新带动新旧生产关系在一个整体下融合,抽取更多新产生的相对剩余价值。资本(广告商)既要抽取绝对剩余价值也要抽取相对剩余价值,所以广告模糊界限的方式出现了。模糊界限,看似模糊的是广告与受众消费的产品、广告内容与产品内容之间的界限,但其本质是在模糊休闲时间与工作时间(劳动时间)之间的差别与界限。“形式上是自由的,实际中却是被强迫的”,智能广告无孔不入的今天,杰哈利的论断更具穿透性地直指今天。彼时有学者指出20世纪电视广告的收看并非强制劳动。但智能广告很多时候都具有强制的性质,今天看似存在与广告“对抗”的手段,但这些手段是由谁生产、出于何种目的生产的?智能广告的“反链接”手段,基本与其“链接”手段是伴生或互补的,如选择关闭、不感兴趣等,本质上是在优化你的广告推荐机制,增强用户与智能广告的互动。智能广告以更为无孔不入的方式,被默认为媒介世界“背景音”般的基础设施而存在。从其无所不在的存在方式,“反抗”即反馈的互动方式下,这何尝不是一种强制与劳动。
在智能广告的用户观看时间上,观看广告时间作为20世纪衡量广告收益的指标,在今天也需要重新打开。杰哈利关注观看广告时间,本质上是对收看劳动产生的时间价值进行衡量,是在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劳动与价值分析。而今天智能广告的收看时间越来越两极分化——极短与极长。按照杰哈利的观点,观看时间长意味着绝对剩余时间的增长,剩余价值增加,而短或“看到就关闭”则意味着广告收看劳动的失败,没有产生剩余价值。但显然这无法解释今天智能广告的收看行为和广告的剩余价值。今天观看智能广告哪怕只是一瞬,或是对广告短暂的“反抗”互动,也会使用户在有意无意间被产品特色的符号“魔弹”所击中。智能广告时代,受众能容忍、接受广告的时间越来越短,看似“对抗”广告侵扰的方法也越来越多。但很多时候看似“对抗”的手段,本质上让受众通过关闭、不喜欢、不感兴趣等方式的“互动”行为与时间产生短暂连接,加深记忆。进而清晰受众自己喜欢的广告类型,优化广告推荐机制,继续推荐更“符合”受众喜好的广告。与此同时,智能广告也在双方互动的摸索中廓清与形塑受众具体而准确的好恶,无形中使“我们”作为智能广告生产环节中的一个生产要素、生产资料,进入生产系统,自我与自我需求的延伸被扣留在广告中,进入再生产与交换价值体系中。大众媒介的主要特征不在于它给了你什么(讯息),而是在于它从你身上取走了什么[30]。
在智能广告的价值增值上,如何理解智能广告中的互动行为与观看时间产生的广告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只看工作日长度而定,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把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构成,彻彻底底地做了革命性的改变。”[31]今天的智能广告往往搭载其他媒介出现,它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是由谁,怎样生产的?智能广告在今天所榨取的往往是受众除必要广告或称必要观看时间之外的“剩余时间”[32],也就是这部分为它们产生了价值。受众观看劳动所产生的观看时间本质来源于剩余劳动时间。以程序化创意为代表的技术变革,使得智能广告的诞生,究其原因是广告商为了抽取除必要广告观看时间的剩余时间所产生的绝对剩余价值,最终走向试图持续增加用户有关广告的劳动,延长广告的总体时间。但现实中广告过多,一方面违反法律及行业规定;另一方面受众也不买账。因此,这就走入了另一个方向,在受众能够接受的尽可能长的广告观看时间中使观看时间内,更加绵密地填充符号与意义,或使其观看得更加认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广告商开始重组受众的收看时间。同时,产生了另一种获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即相对价值的抽取,不延长收视时间,但可以对有限时间尽可能地分割,以满足必要与生与时间的比率。此外,当广告时间能够以较高的费率被媒介出售,受众能够被更高效地组织起来,更全神贯注、更认真,也更为密集和有效地去观看时,由于观看广告时间的价值提高了,必要的收看时间也会减少,剩余的观看时间就会增加,剩余价值也会增加。
基于以上从智能广告生产语境、生产方式,对用户收看行为与观看时间的需要,广告的多重暧昧性也得以充分发酵,具体来说,智能广告依赖于建构想象中的场景,而非作为个体生活的环境;抓住的是瞬时的人的碎片,而非个体的整体需要;强调的是产品的特色,而非其质性的集合。不妨在此做一个反向提问,如若突出产品质性,广告对应的该是此商品可以服务于什么场景、什么人。事实上,今天市面上的广告,大多都在暧昧地突出产品的特色。因为突出特色,吸引用户,才能使得商品真正进入交换价值体系,达成购买,继而再生产这一工业。而商品进入交换体系后,如何交换、什么场景和时间下交换,谁会来交换,这些反过来又都是由用户的收看广告行为与观看广告时间的交换价值所支配的。
5.结语:智能广告时代中“我们就是这样的空隙”
“我们就是这样的空隙”[33],在杰哈利的阐释中商品的价值与意义都被抽空,在被抽空的位置上,是什么填充了这个空隙?生产单位将广告生产成能指,广告又将商品生产成符号[34]。在杰哈利看来,是广告创造了意义,填充、雕琢、抹平了空隙。意义是“我们”创造的,并通过“我们”起作用,这使得广告得以进入交换价值体系,最终商品的价值得以实现。商品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体,商品中不同形式的具体劳动决定了它的使用价值,商品的价值又源于其中凝结的纯粹的抽象劳动,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点。因此,杰哈利要用“收看劳动”与“观看时间”来破解20世纪西方消费社会的广告与拜物现象。“空隙”说只被威廉姆斯和杰哈利一笔带过,但在今天,智能广告让我们在广告的空隙中存在、挣扎也迷醉,我们也让广告越来越变成空隙,变为日常生活中可感觉又超感觉,真实又虚幻的存在。这是今天我们对智能广告又爱又恨的现实状况。
借由杰哈利的理论,剖开空隙,我们能看到的实质是什么?广告通过什么方式侵吞掉真实,再构虚假?广告把商品本身质性所携带的意义,从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的物质环境中抽象出来,远离人或社会现象,这样原本“物”的真实性就会被隐去,变为看上去并不真实的东西。此时,“物”的真实与虚假之间就出现了“间隙”。于是广告进入,蚕食脱离“母体”的真实,再以惯常出现的“真实”的样子,建构出日常文化包裹下,与真实看起来“并无二致”的虚假内容,填充间隙。“让人们感觉到‘我们正在理解(真实)世界’,但其实只是在理解广告”[35]。广告似乎有自己的生命;它从其他媒介来,在此生存,它与我们说话的时候,使用的语言是我们所理解的,但对那种语调我们却从来辨认不出。这是因为广告是没有“主体”的。当然有人制作了广告,但这些人不为我们所知。事实上,广告业从没说过它们代表这些生产者发言,因为广告并不是这些人的言辞。广告的言辞是从我们中剥离出的“需要和享受”,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说,“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生产的,因此,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去衡量的。”[36]广告就是这样预留了一个间隙(space)等待购买者,站出来成为发言人并填充它。当“我们”被拉进去填充这样的空隙。这样,我们既是听众,也是说话者;既是主体,又是客体[37]。因此,广告的力量,从不在于它精巧的创造力,也不在于其能够操纵受众的能力,它的力量在于能够协调意义被挖空又被需要的辩证关系。
归根结底,重新发现智能广告的来处,认识智能广告生产的本质,是唯一坚实有效的认识和反思技术不断变革下广告生产与实践的途径。这不仅是广告创作者与研究者所要面向的挑战,也是智能广告时代的我们所共同需要的追问。
——————
作者简介
刘施阳,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2022级硕士研究生
——————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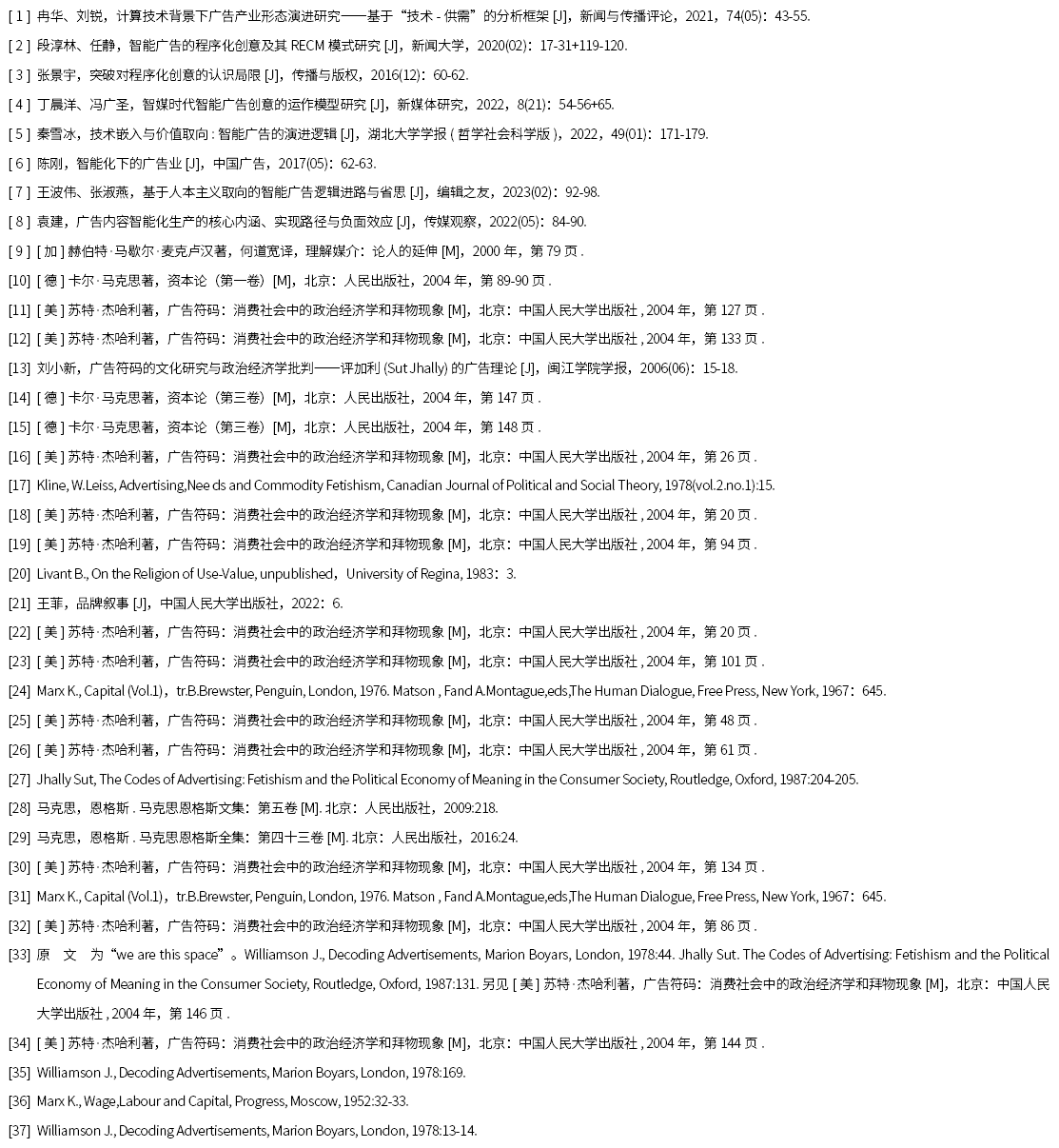
推荐
- 上任一年,雀巢CEO因“办公室恋情”被解雇
- 刘德华在海飞丝发布会上宣布「退圈」、2025亚马逊 Prim
- 人工智能对提升西安文旅品牌新质生产力的路径探索
- 在空隙中: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智能广告生产——关于苏特·杰
- 智能广告背景下重庆地区广告公司转型影响因素模型与转型路径研究
- Cindy Rose 执掌 WPP:在挑战与期待中开启新篇章
- X 发布游戏出海白皮书:叙事力引领中国游戏全球化,AI 重塑
- 2025 釜山国际广告节传捷报:中国选手包揽 New Sta
- 稳健前行,比音勒芬多维布局高端运动户外新格局
- 安踏集团与韩国潮流电商平台 Musinsa 成立合资公司
- 萨尔瓦多迎来沃尔玛2.6亿美元五年投资大计
- RIMOWA Hybrid系列推出限定色天空蓝
- 卸任Grey 和AKQA中国区CEO 后新动向!Sharle
- 投流费“归位”:广告合规新纪元开启
- 从厌学到复学|08 如何从“监工”到“盟友”,让孩子愿意聊学


